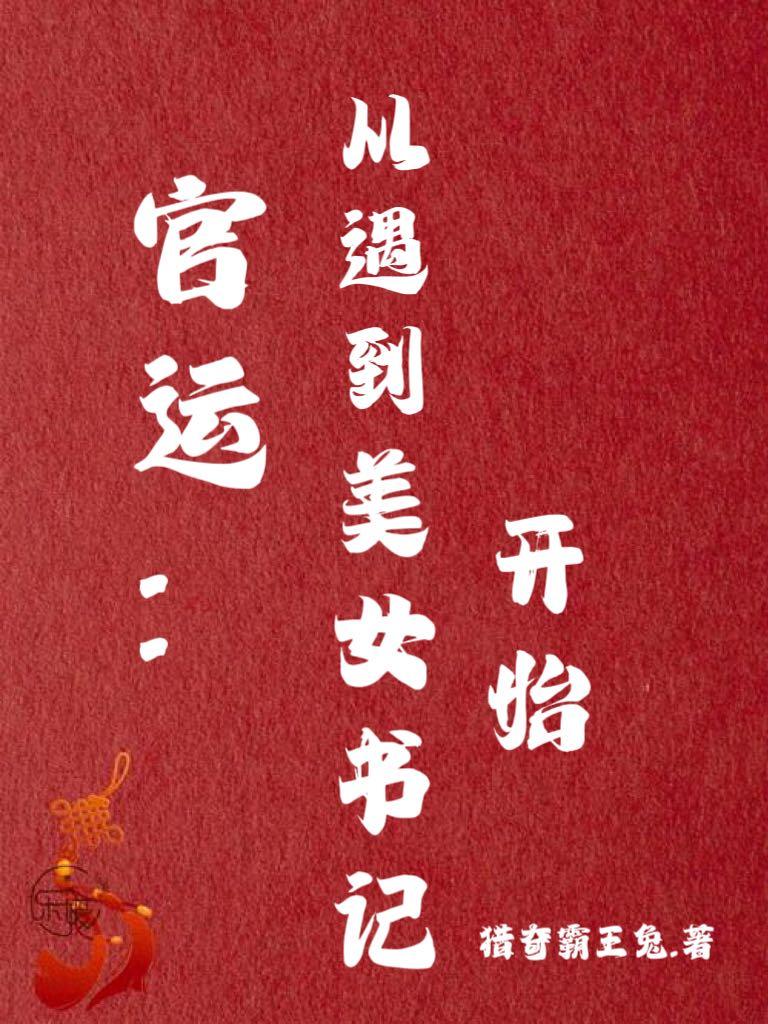我趕忙跟着彪哥回了他住的木屋。
推門進去,我第一眼注意到的,是牆上挂了幾個木頭牌子,一問才清楚,他是采用翻牌的方式來決定今晚找哪個老婆,就跟古代皇帝選妃一樣。
夏兒巴人成熟都偏早,他小老婆比彪哥小十歲左右,身高也比他高半個頭,皮膚呈現健康的小麥色,鼻梁挺,眼睛大,嘴唇薄,典型的少數民族長相,她不會說漢語,但因為和彪哥在一起兩三年了,能聽懂一些。
進來後,我不太敢正眼看他小老婆。
她穿的過于少了,我怕盯着人看,會讓人覺得不受尊重。
“老幺,我的筆記本放哪了?怎麼找不到了?”
彪哥拉開抽屜,翻箱倒櫃找了半天,又跪在地上在床底下翻包。
他小老婆雙手捧起來油茶喝了一口,翹着二郎腿,輕聲哼唱着某種夏爾巴歌曲,看起來很放松。
“找到了!原來我放這兒了!”
從床底下的包裡掏出來個厚本子,彪哥撕下來幾張白紙,連同圓珠筆砰的放在了桌上,大聲說:“快畫!老幺!我說你畫!”
二人當着我的面兒交談了幾句。
當聽到彪哥要畫“那個男人”,他小老婆臉色瞬間變的極其難看!在沒有了剛才唱歌時的放松狀态。
她憤怒的說了幾句,起身便向外跑。
“回來!”
“我的話你都不聽了是吧!”
彪哥把人拉回來,揚手說:“我打你信不信!”
這女孩兒比彪哥高半個頭,毫不畏懼,瞪着他看。
“呵.....”彪哥踮起腳尖親了人一口,笑着說:“老幺别生氣,我最喜歡你了,疼你都來不及,怎麼舍得打你呢。”
“兄弟你先出去等兩分鐘行不?我做做她工作。”
“好。”
我出來關上門,看着黑暗中的弭藥山,皺起了眉頭。
七月爬很神秘,我有自信,隻要看過他的畫像,但凡有四分像,在見到他時,我就能認出來。
在門外等了幾分鐘,彪哥喊我進去,說已經做通他小老婆的思想工作了。
我問他:“為什這麼害怕七月爬。”
彪哥猶豫了幾秒鐘,開口說:“兄弟,有些情況你不知道,我這次幫你冒了很大風險。”
“我在這個部落已經四年了,當帝師已經三年了,我心底最怕的,就是某一天見到兩個人,一個是康定派出所的人,在一個....就是七月爬。”
“我感覺,他不是人。”
“什麼意思?”
彪哥皺眉說:“就是字面上的意思,以前部落裡有幾個年輕人不服氣,說要收拾他,結果後來幾天,那幾個夏爾巴小夥子要麼淹死在了河裡,要麼睡死在了木屋裡,當時我親眼看到屍體擡出來的,他們眼睛瞪的很大,像是死前見了鬼。”
“還有,他們身上有留了一個記号。”
說完,彪哥手在半空中,畫了個倒三角形。
“你知不知道,這個是什麼圖案?”
我搖頭。
彪哥臉色凝重:“我問了族裡年紀最長的老人,老人說這個圖案是屬于古黨項人的,代表的意思,是守護和詛咒。”
“守護?守護什麼東西?”
彪哥搖搖頭,讓我進屋後,他又反鎖上了木門。
屋裡。
桌子上點了兩根蠟燭,鋪了一張白紙。
彪哥老婆低頭在白紙上寫寫畫畫,她時而收筆停下,仔細聽彪哥說細節。
彪哥沒說謊,這女孩兒畫畫真好,她沒學過美術什麼的,可能這就是天分,簡單的幾條線條,就能勾畫出一個人的臉部輪廓。
“不對.....鼻子不是這樣子的,應該更挺一些,下吧也不對,下巴有胡子,應該是那種摸起來會紮手,很硬很短的胡子。”彪哥說。
他小老婆将畫紙揉成一團,又重新鋪開一張白紙,繼續畫。
警察有這種畫畫技術,但畢竟我們不是專業的,隻能摸索着去畫,彪哥努力的回憶說出各種細節,他小老婆也很努力的幫忙畫。
從臉型,發型,在到眉毛,嘴巴。
廢紙丢了一張又一張,彪哥總是說:“不像....還不像,是不是我遺漏了什麼....可能是眼睛部位出問題了,老幺,你先别畫眼睛看看。”
再次畫好一張。
彪哥砰的一拍桌子,激動說:“對了對了!兄弟這次對了!就是這個人!”
我看向白紙。
這是什麼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