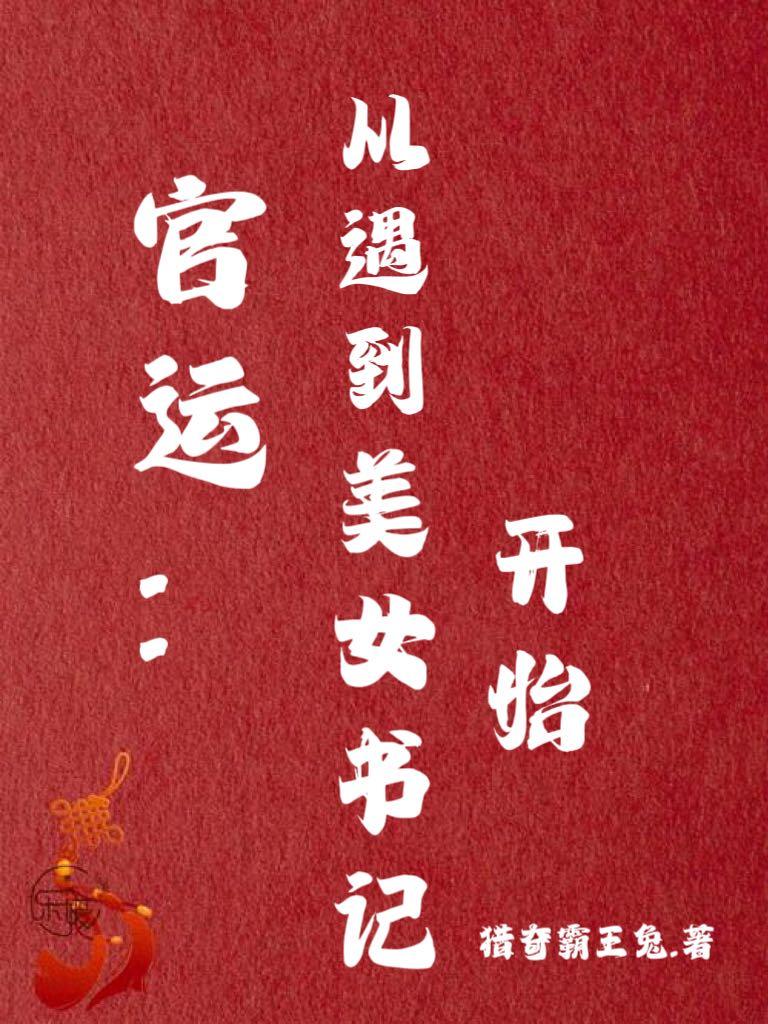c紅姐和陳建生都是三四十歲的人了,說吵就吵,若外人見了肯定會說這二人沒風度。
我不這麼看。
他們都是盜門中人,是江湖人,三教九流,身上都帶着下層社會的痞子氣,這點是很難改變的。
我接連解釋了幾次,紅姐這才明白過來。
“呵....”紅姐冷笑譏諷道:“我說呢,怪不得老學人說話,原來是個二百五傻子,算了,不跟這南派傻子一般見識。”
“這就對了嘛,”随後,我指着河對岸問:“紅姐你說,咱們怎麼過去?”
“哦?”她皺眉道:“過去幹什麼,你難道真信這傻子說的?”
想了想,我點頭道:“紅姐你沒注意到?那些幹柴是哪來的?我覺得這人說的可能是真的,這裡,可能還藏着别的秘密。”
陳建生還在發傻,還在學我們說話。
一顆痣轉身看了他一眼,一咬牙,道:“行,雲峰,你信他,我信你,那咱們就遊過去看看,看看裡面是不是别有洞天。”
“雲峰你水性不好是吧?”她問我。
“嗯.......不是不好,是連狗刨都不會,”我苦着臉說。
她無奈道:“不是我說你雲峰,要是咱們找到老三他們出去了,你以後可得練練水,幹這行,不會水,遲早得吃大虧。”
“你從後面抱緊我,我帶你過去。”
我忙點頭說好。
這段地下河不寬,但水很深,這個時節水溫也很低,紅姐水性是好,但她也不敢托大。
“你小子往下點,手放哪了。”
“哦,哦,對不起紅姐,”我忙把手往下移了移。
下水之前,我回頭看了眼神智不清的陳建生,就問道:“紅姐,那這男人怎麼辦?把他留這?”
“鹹吃蘿蔔淡操心,”她冷着臉說,“南派的土工,死就死了,不用管他。”
“哦.......”我也不敢頂嘴。
回頭深深的看了一眼這男的,我深吸一口氣。
“噗通一聲,”我抱着紅姐,一塊跳進了地下河。
河水比我想象中的還冷,不過幾十秒的功夫,我就感覺自己凍的手腳發麻。
“集中注意力,别松手,過去就好了,”紅姐就這麼馱着我,一點點向河岸邊遊去。
我們運氣不錯,這次沒出什麼岔子,不到十分鐘,我們平安上了岸。
擰幹了衣服,我兩走到了那條裂縫跟前。
這山縫十幾米高,從外面看非常深,寬度一次隻能通過一人。
檢查了下手電的電量,還能亮,但光源已經很散了。
我和紅姐彼此對視了一眼。
我點點頭,率先側着身子鑽了進去。
順着山縫往裡鑽的時候,我一直收着肚子,因為這山縫裡有些凸出來的碎石,我碰到了幾次,咯的肉疼。